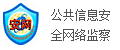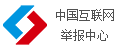晨读|酱菜锁忆
来源:互联网 阅读:0
回忆中的酱菜是一种乡恋,它五味杂陈,却又绵厚深长,远胜于一席精致的宴席。

“没有酱菜的宴席是不完整的”,这是一位名人说的话。但我对酱菜的感受,远不止于这一点。
我从小在农村长大,曾度过一段很长的苦日子。那时,乡里人家的饭桌上,极少有鱼肉荤腥,一日三餐,除了些杂七杂八的菜蔬,有时就靠着酱菜喝粥下饭。
在我吃过的酱菜中,酱瓜的档次是最高的,但它又绝非像刘姥姥在大观园里吃过的那道茄鲞娇贵:“我的佛祖!倒得十来只鸡来配它,怪道这个味儿!”
酱瓜,是靠着阳光、晨露和清风滋养出来的,一如庄稼人的质朴淳厚。每年黄梅季节将至,乡里人家就开始做酱爿了。把面粉揉成软硬适中的面团后切成片,在沸水里煮熟了,捞到饭箩竹篓里,冷却后挂在横梁上或搁在一旁。黄梅一过,面片全发霉了,等用清水洗刷干净周身露出浅灰色,这便是酱爿的真身了。
酱缸也在这时粉墨登场。它们被搁在场头的砖垛或木架上,大半缸清水里加上粗盐,搅匀后把酱爿放进去,不消两天的日晒夜露,它们就融为淡黄色的面酱。以后的日子里,主人家就只管放料,黄瓜、菜瓜、茄子、西瓜皮等等,这些物料之前已经腌过一夜半天的,被放到酱缸里后,三四天就化身为酱瓜啦!
就这样,在整个夏季,一批酱瓜被捞出,一批瓜料又被投放进去,如此循环反复,直到一缸面酱成了绛紫色,腌出来的酱瓜照样好吃。只是有两点,一是烈日当空面酱正发烫时,不能轻易惊动它;二是下雨时,必须防止雨水侵入,否则面酱就会变质,食之酸涩,弃之不舍。所以,那段时间里,只要老天一下雨,场头上家家户户的酱缸便被戴上了“帽子”,高高低低的,煞是好看。
比起酱瓜,萝卜干的制作显然简单了许多。把白的、红的、青的萝卜洗干净后切成条,腌上二三天,捞出来风干后,就可以严严实实地塞到瓶子瓮罐里了。这时倘若拌入一点瘪谷茴香,腌成后就咸里带香了。
萝卜干的最大缺点,是吃多了容易糟心反胃;但也有一个最长处,可以随手用纸头什么的一包,放到口袋里当零食吃,寡淡的嘴巴里于是就少了寡淡。
“外国姜”是哪年被引进的,我已经记不清了。外国姜的根茎状似生姜,但不辛辣,肉质嫩,且喜长,一窝窝的,用来腌制酱菜,非常爽口,价廉物美。
至于咸菜,对,那些被乡里人家叫作“盐齑”的咸菜,它怎么可以被忘了,但它又算不算酱菜一族呢?
那时候,每到初冬,乡里人家都会腌制咸菜。用一口偌大的水缸,把洗净风干后的大青菜、雪里蕻等绿叶菜铺进去,撒上盐,随后有人赤脚跳到水缸里使劲地踩,但等踩出水来,再铺上一层菜一层盐,层层叠叠的,直到踩满一缸,最后顶上压一块大石墩。半个来月,一缸咸菜就开吃了,一吃就吃到来年的春天,吃不完还可以洗干净切碎了晒成咸菜干。
那时,少不更事的我也曾帮着母亲一起腌咸菜,赤着脚板跳进水缸里,双手舞动着,嘴里发出“喝哧喝哧”的声音,累着,但好像也快活着。
多少年过去了,这样一种苦中作乐的场景,至今犹在眼前,那一段“酱菜岁月”,也始终挥之不去。前不久,有位文友在微信群里晒出一瓶酱瓜:“我老妈做的,太好吃了!”我不禁回复一个表情包:“久违了,让我口水直流。”没想到的是,这位文友不言不语的,却在几天后出其不意地快递给我一瓶同样的酱瓜,打开瓶盖,一股异香,满是回忆。
这些回忆,也就是一种乡恋吧,它五味杂陈,却又绵厚深长,远胜于一席精致的宴席。(赵荣发)
推荐阅读:旗龙网